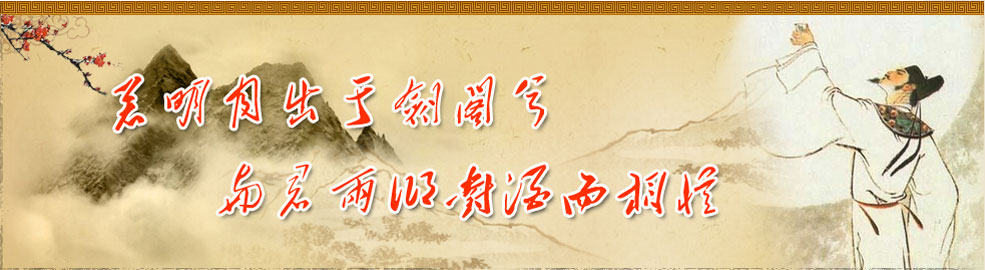李白文化研究2008年集序言
薛天纬
去年11月,接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来信,告以中心作为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即将召开课题研究学术交流会,会后拟编辑出版《李白文化研究》第一辑,嘱我为序。09年伊始,即收到编就的会议论文集。我忆起2006年春在江油参加了李白文化旅游节的学术活动后,曾顺道至绵阳,访问刚刚成立的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当时情景尚历历在目。中心成立之初,百事待举,面临许多困难,就连最基本的办公场所都显得局促而简陋,但是,中心同人的热情很高,颇有摩拳擦掌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时间转瞬过去了两年多,得到中心举办这次学术交流会的消息,十分欣喜,当然没有理由不去勉力完成中心交给自己的任务,因承乏为序,谈谈在拜读了会议论文后的感想。
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对于李白文化的研究,这是当前李白研究的新潮和热点。“李白文化”是一个新语词。什么是“李白文化”?我个人的看法,对于这个命题似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李白文化”概括了李白研究的全部内容(历史的与现实的、学术的与应用的、文本的与接受的等等),因为李白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人,他留给后世的是一笔文化遗产。“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之命名,应该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标举“李白文化”。狭义的“李白文化”,核心是指李白精神,这种精神为李白所独具,是李白区别于、并超越了中国古代其他文化人(包括其他杰出文化人)的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李白之所以为李白,即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李白文化研究,至少包括了对李白精神的历史阐释和现代弘扬两个方面。我这里讲“李白文化”,取其狭义。对于李白精神的研究,并非始于今日,试从上世纪说起,影响最著者,三十年代李长之先生有李白是“疯子”与“狂人”之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五十年代初林庚先生有“布衣感”之说(《诗人李白》)。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语境的变迁,对于李白精神的研究日趋活跃。这是因为,李白精神说到底乃是人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对人性的终极追求,而现时代正是一个提倡以人为本、弘扬和光大人性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明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李白精神得到重新认识和深入开掘,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裴斐先生说:“如果不是从唐代历史,而是从整个古代文化背景上看,李白亦无愧于先觉者。我指的是人的自我和个体人格的觉醒……在封建专制文化——其基本特点就在强调思想统一,崇尚社会伦理而抹杀个体人格价值——的禁锢下,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一个个体人格意识十分淡薄的民族。正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上,李白的出现犹如漫漫长夜升起的一盏明灯、一颗巨星。”(《李白个性论》,见《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林继中先生指出李白的人格理想“让人格独立与社会关怀结合起来”,是一种健全的理想人格。(《“布衣感”新论》,见《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马力先生则说,李白的意义“在于他具有推翻封建制度的潜在因素”,“还在于他浓厚的主体意识、自我扩张的现代型人格。这种人格必然导出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和平等又是民主和科学的温床。”(《文化漩涡中的溺水者》,见《中国李白研究》2000年集)这些论述,都是对李白精神的精辟分析。何念龙先生即将面世的著作《李白文化现象论》,更是对李白精神的全面阐发。这次学术交流会上有多篇专门探讨李白文化和李白精神的论文,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如杨学是《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在宏观而又周密地探究了“李白文化”的内涵、回顾了现时代“李白文化”研究状况的同时,将关注点集中于李白“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人格”,这正指向了李白文化的核心。郭名华《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下李白文化的尴尬处境》指出,“李白精神是李白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李白豪迈的性格,济世的精神以及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所构成的李白文化精神内涵,正是我们时代先进文化建设所需的重要源泉和动力”。陈明彬、资建民《李白青少年时期文化心理个性特征》说,李白“一生在行事上,在诗歌中总是执着而顽强地张扬着一个声音:人格平等”。陈建新、谢莉《李白精神的现代认识之我见》说,“理性与本能,本是人身上的两种属性,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自然本能成为了异质,遭到了压制。而在李白身上所体现的异质性,就是对生命本能的张扬”;“一旦要在理性的生活与天性的放纵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李白总是选择后者”。又说,“李白全部的艺术与人生,都是实现自我的拯救的一种努力”,而“李白自我拯救的方式,就是张扬非理性的、来自于本能的激情,以摆脱现实生活对生命的压抑。这种拯救的方式,是现代性的,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苏焘《李白现象之文化心理取向的生成及演进试探》分知识层和平民层两个群体来考察后世人们对李白文化现象的接受与认同的心理特点:关于前者,在“道”与“势”抗争依存的矛盾中肯定了知识层对李白豪纵之风、逸荡之气的肯定;关于后者,则归纳为身份认同、圆满趋向和神秘性。几篇属于比较研究的文章,也都贯穿了对李白精神的探讨和阐发,如梁光焰《郁达夫与李白的精神气质比较》说:“李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解放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布道的精准表现,他的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幻想人格,他的自由人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后堡垒。”又说:“自由人格严格说来是一种理想,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才是历代知识分子所苦苦以求的。这是知识分子从古至今化解不开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知识分子痛苦的根源。”这些论说对李白精神的理解各有其精到处,并且都不乏理论色彩。由此可见,关于李白精神的基本内涵大家是有共识的,而且对李白精神的阐释与开掘在不断深化。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吴增辉《李白安史之乱后诗歌及心态的文化解析》。正如题目所示,这篇文章的审视对象,是“安史之乱”后李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如《猛虎行》《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这些诗篇对战乱时局、对叛贼暴行、对民生苦难等社会现实均有直接反映,对平叛报国的期盼和抱负也有直接抒写。研究者们对此一向特别重视,并从传统的“思想性”标准出发,给予高度评价。吴文对传统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颠覆:第一,文章当然并不否认“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李白诗歌开始渗入更多的现实因素”,但是认为“现实内容的增强是一种强行的介入,对诗人而言则是被动的接受”。文章说:“李白已经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营造诗歌语境,对外在现实因素的强行介入及其对‘自我’的挤压有一种几乎本能的排斥,因而李白仍然竭力把这类现实内容纳入到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叙事框架中,使之成为‘自我’活动的背景,并自然而然地楔入他所熟悉的饮宴作乐的生活”,“这种作乐场面与动乱的时局显然极不谐调”。第二,“李白对朝廷与叛军双方态度的超然及对涉及朝廷安危的重大事件的淡漠”。以上两点,给人的感觉都是从“负面”评说李白,做出这样的评说是需要一些胆识的(关于第二点,用词是否过头?可再酌)。应该说,吴文指出的两点,确实是李白诗歌中的实际存在,关键是对此如何解释。关于诗中的宴乐场景,笔者就曾说到过(见与安旗、阎琦合著《李诗咀华》,书中《扶风豪士歌》一篇出自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段闲笔”,“这些诗句并不意味着李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而寻求个人安乐,这不过是即事即景的一般应酬之词罢了”。关于李白对唐王朝和安史之间的战争的看法,周勋初先生曾有论及(见《诗仙李白之谜》第九章),指出李白将之看作楚汉之争是犯了“历史类比”的错误,同时,还征引了范文澜的相关说法。吴文则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释的。关于第一点,吴文说,这是李白的盛世心理,是李白身上所体现的盛唐文化精神。而“所谓盛唐文化精神,实则是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所激发出的人的蓬勃的生命激情的外在展现,它使个体倾向于个性的强烈伸张及精神自由的无限延伸”。再做进一步的文化解析,吴文的看法是:“李白基于道文化的独立自由人格使他不可能实现由个体到群体、由自我到社会、由盛世到乱世的彻底转向,则其诗歌对现实反映的广度与深度必然仍是有限的”。关于第二点,吴文做出的文化解析是:“李白对朝廷安危之淡然超然在深刻意义上又表现出道文化以自然自由为核心的哲学观对儒文化以秩序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的严重消解,及由此而形成的李白对儒教道德秩序及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的背离”。吴文还将李、杜诗歌对安史之乱的反映做了对比,并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李杜二人在文学史上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在深刻意义上象征了中国文化精神由浪漫向现实的衰变过程。”关于道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关于李、杜创作倾向的不同,自然并非吴文的发现,但其从文化高度并从特定政治背景下之李白诗歌创作实际出发所进行的文化探源,确有发人所未发处,因而显示了独到与深刻。文化探源则反过来加深了对诗歌文本意义的准确解读,“负面”的感觉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围绕李白精神和人格来研究“李白文化”,要旨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下,来探讨李白文化的历史价值、现代意义乃至未来意义,从而汲取其积极内核来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绝不能实用主义或急功近利地看待这件事,不能希图这种研究的应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图李白成为一个当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对“李白文化”热,这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清醒和沉稳。
其次,是实证性研究方面的成果。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杨栩生、沈曙东《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以下简称“杨文”)。这是一篇挑战性与严谨性兼具的论文。《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的名作,为古今读者所熟知。然而,自从詹锳先生1983年在《文学评论》发表《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一文后,其结论遂为李白研究界以至唐诗研究界普遍接受。二十多年来,鲜有不同意见。杨文可以说是首次与詹锳先生权威性的观点进行认真商榷,因而具有挑战性。杨文考证之严谨性,可于几处着力点见之,如:《文苑英华》题注“集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所指“集”即始于乐史、终于宋敏求、曾巩的《草堂集》;“蓬莱文章”点出了李云校书郎身份;李华虽擅碑铭,但并不闻名于李白之时,而是至德二载以后事,所以,《文苑英华》以“蓬莱文章”为“蔡氏文章”属编纂之误;《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与《饯校书叔云》非一时一地之作,等等。这些考证都很见功力。杨文既出,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李白这一名篇题目乃至内容进一步的思考和认识。由于李白生平家世及诗文版本等传世原始资料有限,实证性研究在李白研究中一向具有“攻坚”性质。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这种情势下,每前进一步都非易事。因此,我们绝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指望突然间会有惊人发现。只有付出较之前人更为扎实而严谨的功夫,才可能有或大或小的收获,而每一或大或小的收获都是令人欣喜的。杨文在这方面正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杨文之外,康怀远《“专车之骨”臆解》和殷春梅《李白〈横江词六首〉与横江风波题材诗歌》在实证性研究方面也各有所获。
论文集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李白文化研究中心正在按照自身规划,展开一系列课题研究。这些课题的设计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如《李白年谱汇笺》,是综合性的大题目,“年谱汇笺”这种形式从学理上说,几乎要吸收李白生平及作品研究的全部有效成果,于折中取舍间表明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可能成为集古今李白研究精华之大成的、具有空前意义的学术著作。《李白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从一个特定视角展开,与李白家世、生平和诗歌创作密切相关,也具有综合性与全局性。《李白诗歌俗语研究》《李白诗歌词语特色研究》是从语言学角度对李白诗歌语词的专门研究,前一成果对于理解李白诗歌俗语更可能具有某种“工具”性质。《李白文化数据库建设》是一项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的基础性资料收集与整理工程,预期中的成果将给李白文化研究提供巨大方便。《李白与巴蜀资料汇编》《李白故里语言文化研究》更是绵阳学者的“专利”和强项,有关专家长期潜心于此,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李白研究方面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特有的权威性。总观这些课题,命意新颖,视野开阔,既富有故里特色,又立足学术前沿。本次学术交流会已展示了一些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如果各项课题顺利完成,必将填补李白研究的许多空白。李白文化研究中心以一所综合性高校为核心,集结周围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发挥各自优势,以课题的形式做出系统设计,实行多层次、多方位、多学科的战略性展开,这在国内的李白研究全局中尚属首创,也非其他地方所能轻易效仿。可以预期,随着这些课题的完成,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将成为国内李白研究的重镇。
论文集中还有从旅游及英语翻译方面进行研究的两组文章,由于专业所限,我无从置喙。但这些研究对于李白故里的文化和经济建设、对于李白作品的全球性传播,无疑具有促进作用。有篇题为《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与李白文化旅游灾后重塑形象的可行性分析》的文章,把我们的思绪带回了去年5月,那场“地崩山摧”的大地震使李白故里经历了一场劫难。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曾多次到江油瞻仰李白遗迹和参加学术会议,对那里的山川风物有无比美好的记忆。我无法想象那些与李白相关的文物古迹及园林建筑遭到破坏的景况。李白故里的人民(当然包括绵阳的李白研究者们)当前正肩负着艰巨的重建任务。我相信,不要太久的时间,当我再次踏上李白故里的土地时,遭地震毁坏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景观将得到很好的恢复和更好的建设,故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将得到更充分的开发。这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珍贵遗产与李白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业绩相辉映、相交融,李白精神在故里必将迸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2009年3月)